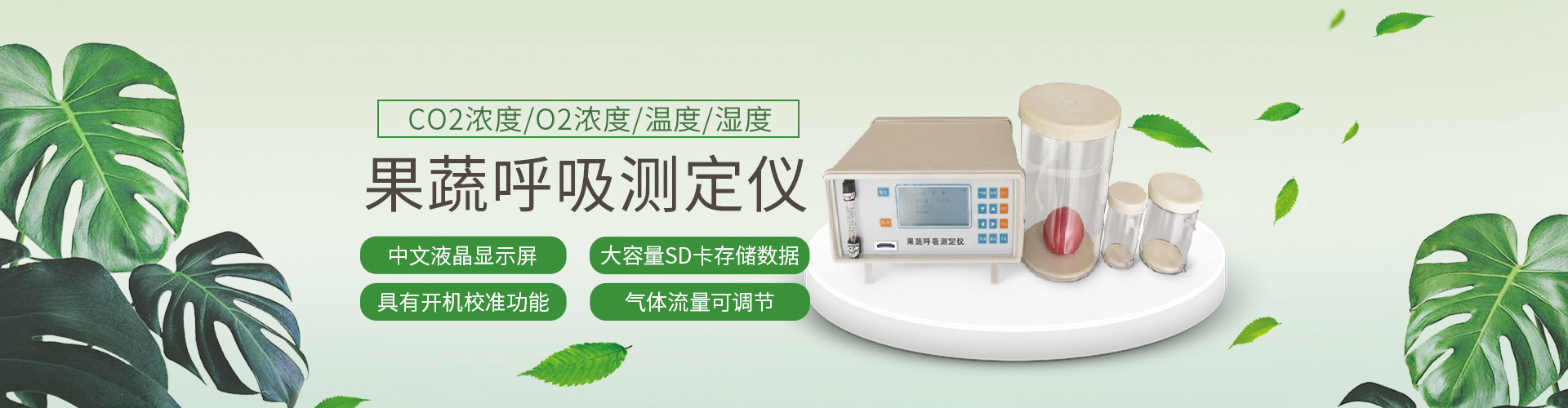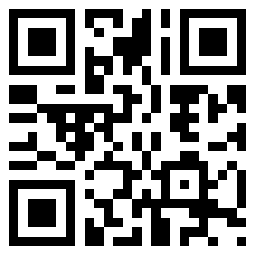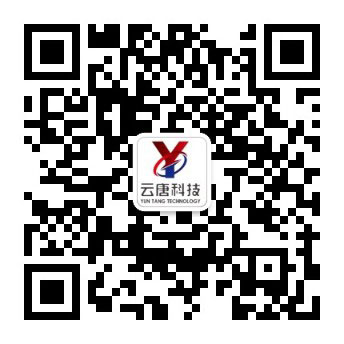电力局稽察员上门指着电表痛斥我偷电勒令我补缴十倍罚款
产品简介: 厂里凡是跟电有关的难题,从苏联老大哥那会儿传下来的机床,到新进的德国设备,最终总得我来收场。 它现已空了好久,院里的野草长得比我还高,墙皮斑斓,显露里边的夯土,像白叟的皮肤。 我把一切积储都拿了出来,买了其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国标紫铜线、阻燃穿线管、还有簇新的空气开关。 强电、弱电,分路、走线,每一个插座的方位,每一盏灯的功率,我都算得清清楚楚。
产品详情

厂里凡是跟电有关的难题,从苏联老大哥那会儿传下来的机床,到新进的德国设备,最终总得我来收场。
它现已空了好久,院里的野草长得比我还高,墙皮斑斓,显露里边的夯土,像白叟的皮肤。
我把一切积储都拿了出来,买了其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国标紫铜线、阻燃穿线管、还有簇新的空气开关。
强电、弱电,分路、走线,每一个插座的方位,每一盏灯的功率,我都算得清清楚楚。
我的方案很清楚:内部线路悉数竣工,请电力局来检验,合格了,再请求装新表,通电。
那家伙“突突突”地响,耗油,还招人嫌,但它是我这片漆黑工地上仅有的光源。
到了晚上,特别夜深人静的时分,还能模糊听到他那儿传来继续的“嗡嗡”声,消沉,但很有穿透力。
可看着屋子里犬牙交错的线管,像一幅未完成的抽象画,我心里,竟生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安定。
紧接着,一辆半旧的绿色吉普车,车门上喷着“电力稽察”四个白字,粗犷地停在了胡同中心,堵住了大半个通道。
他死后跟着个年轻人,戴着眼镜,一脸怯生生的容貌,应该是新来的,我后来知道他叫小周。
“下岗了没钱,就动这种歪脑筋了是吧?在厂里当电工,把手工用到这儿来了?”
“你看看!你给我看看!这电表转得比风车还快!偷电偷得这么明火执仗,你当咱们电力局的人眼睛都是瞎的?”
咱们的目光,先是落在八面威风的马成功身上,然后,齐刷刷地投向那个飞转的电表,最终,聚集在我身上。
马成功从他那被肚皮撑得紧绷的口袋里,掏出一个黑色的封皮本,和一个计算器。
那个叫小周的年轻人,好像想说什么,他张了张嘴,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马成功。
“依据咱们电力法规的规则,关于窃电行为,不但要补缴所窃电量电费,还要处以三到十倍的罚款!”
“我给你算算,”他抬起头,脸上带着一丝严酷的爽快,“你这电表这个转速,一天最少要跑上百十度电。你这房子空了多久了?咱们从体系里查,最少半年没交过电费了!就算你偷了三个月,每天一百度,这便是九千度电!”
“工业用电一度一块二,便是一万多块钱!咱们从宽处理,不给你算十倍,就算你五倍罚款!加上补缴的电费,你一共要交六万块钱!”
九十年代初,六万块钱,对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来说,是一辈子都未必能攒下的天文数字。
“马……马组长,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搞错了?卫东不是那样的人……”她小声地辩解,声响弱得像蚊子叫。
马成功眼睛一瞪:“搞错?电表会搞错吗?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电表更是大公无私!你看看它转的!”
“陈卫东,我告知你!”马成功的口气变得更严峻,“今日,你要是拿不出钱来,咱们就只能走程序了!”
“报公安!”马成功直截了当地说,“依照偷盗国家财产罪处理!你这数额巨大,够判你几年的了!到时分,可就不是罚款这么简略了!”
就像在工厂时,面临一台完全停工的杂乱机器,一切人都束手无策时,我心里的那种感觉。
那烟雾在我面前升腾、充满,像一道柔软的屏障,暂时隔开了马成功那张油腻的脸,和周围那些杂乱的目光。
“,”我的声响不大,但在这安静的宅院里,每个字都明晰地传到世人耳朵里,“你先别激动。”
“没通电?”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声响都变了调,“你糊弄鬼呢?你当我是三岁小孩?没通电,这电表自己会转?它是靠爱发电啊?”
他气得笑了起来,指着我,对周围的人说:“你们听听!你们都听听!这是下岗工人吗?这是个骗子!死到临头了还嘴硬!”
“给我进去搜!”他大手一挥,对小周命令,“把他的接线板、电器,都给我找出来!我今日就要让他人赃并获,心服口服!”
“马组长,”我安静地说,“有劳您细心看看,我这进户线,有一根,接到您那个电表上了吗?”
也便是说,外墙上那个张狂滚动的电表,流过的一切电流,根本就没有进入陈卫东的房子!
“马组长,”我的口气仍旧安静,但多了一丝技术人员特有的谨慎,“电表在我的墙上,但电,没进我的屋。这种状况,只要一种解说。”
“那便是,有人在电表的前端,也便是从电线杆到这个电表箱的这段主线上,并了一条线出去。”
“这种偷电方法,行话叫‘主线搭火’。它绕过了用户自己的电闸,直接从源头盗取电能。而更偶然,或者说更恶劣的是,作案的人,把计量设备,也便是这一个电表,过错地……或者说,是故意地,接在了我这户的名下。”
这说明,他这个稽察组长,不只委屈了好人,还对真实专业的窃电方法一窍不通。
它的结尾,则一路贴着墙角,绕过院墙,消失在近邻,刘二虎家宅院后方那个整天紧锁的小屋里。
查错了案件,委屈了人,这事传出去,他这个组长的脸没当地放,年末的评优评先更是想都别想。
这个刘二虎,在片区里是出了名的“地头蛇”,传闻他有个表哥在区里某个部分当差,尽管官不大,但要给他这种底层小干部穿个小鞋,几乎一挥而就。
“咳……这个状况,很杂乱,”马成功清了清嗓子,尽力让自己的声响听起来镇定一些,“咱们应该……需求回去再研讨研讨,从长计议。”
宅院角落里,那台我托了多少联系,才装上没几天的黑色旧式转盘电话,忽然声嘶力竭地响了起来。
在一切人猎奇、探求的目光中,我放下东西,擦了擦手,走到墙角,拿起了那个沉甸甸的听筒。
电话那头,是一个沉稳厚重,带着显着知识分子口音的男声,口气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望,和一丝不易发觉的谦让。